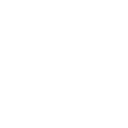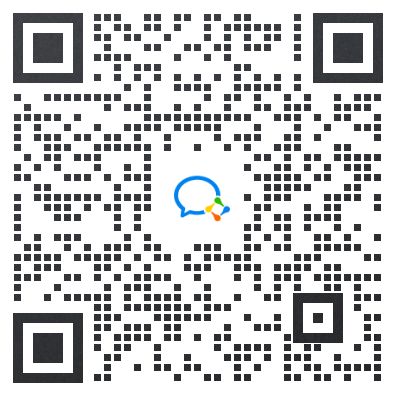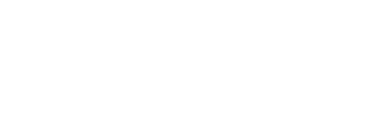真实案例|同性HIV(艾滋病毒)携带者在澳洲的婚恋故事
2020
真实案例
- 同性艾滋病毒携带者在澳洲的婚恋故事-
编者按:
处在这个角度,AHL法律亲眼见证过许多
很残酷、很无奈的东西,
而法律无法改变它们。
愿将之留存,
以警醒和帮助我们所有身处困境、求助无门的华人同胞。
1.从一个夏日开始
我是个喜欢甜食和女人的女人。
千禧年初的一个黄昏,我有点饿,从T站上约了一位隔壁学校的女学生出来陪我吃冰淇淋松饼,她瘦瘦小小,脸色有些倦意,好像刚结束一天的课程。我们坐在落地窗边,聊天,交换秘密,讨论国际形势和布里斯班比较好的几家lesbian bar,看天色一点点变暗。
她叫小辛,肤色白,整条街的霓虹灯在她脸上淌下淡淡的柔光,像朵水仙花儿。
那天我总是止不住地露出笑来。
她是我的类型,更重要的是,她说她知道怎样做松饼,而我说过,我也同样喜欢甜食。
我们开始频繁地吃甜食,从黄金海岸吃到威灵顿港,整个夏日,我开着我的绿漆小破车去她家楼下接她。后来渐渐地,她开始做给我吃。她住在昆士兰大学旁边老式的公寓楼,楼梯间铺满了厚厚的米黄色地毯,脚踩上去会腾起一阵灰尘。屋子里没有空调,开着阳台门通风,只涌进阵阵热浪,我们穿漂亮的小吊带在厨房接吻,拥抱的时候,彼此肌肤上的汗珠细密地融合。
我说我父母离异,我从小和妈妈过,妈妈恐同。
她说没事,都会没事的,一切都会好的。
就这样,从2006年最熟最烂的夏天起,我们开始了漫长的赛跑,和我们的爱,也和我们普通但彼此拯救的人生。
毕业后,我进了银行,她筹钱开了一家奶茶店。我们搬到一起住了,偏远地带一个廉价合租房,半夜常有肥蟑螂爬进卧室,那蟑螂到处逃窜有小老鼠那么大,每次都是我爬起来打,因为她很辛苦,每天早晨六点要起床去店里卸货,煮好各种小料,培训员工,做好线上社群运营。
那段时间经常发生华人商店抢劫事件,所有做小生意的华人都人心惶惶,她也忧愁,一天到晚皱着个小眉头,最后只能在店内装了个摄像头。她心里的弦一直紧绷着,我没什么办法,只能从银行下班后,去肉店买大骨头,熬汤给她喝,煲一个小时,她就到家了。直到现在,我每次煲汤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,因为那是她到家的时间。
14年除夕,因为一直在亏钱,她把奶茶店卖掉,呆在家里待业。那段时间家里的餐桌上经常全是鸡,因为澳洲的鸡几乎是最便宜的一种肉,一大盒鸡肫只要3刀,是牛肉的零头。她就变着花样炒鸡肫,烧鸡翅,凉拌口水鸡,鸡骨熬汤。
她很聪明,我一直都知道。
有她在,两个年轻人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也不算太窘迫。那时候家里的冰箱塞满了东西,到最后蔬菜常常不新鲜,因为为了省钱,她每个月都开我那辆绿漆小破车去批发市场买最便宜的蔬菜,一买就是一大箱。回来的路上,后备箱半敞着,合都合不上,跑在公路上像只张口的坏鞋。
这段困顿的时间里,家里还闹起了鼠灾,不知道从哪个下水道或者门缝里钻进家的老鼠,开始在屋子里繁衍后代扩大家族。我们为了削减开支,不敢请灭鼠团队,就上YouTube学习怎么自制捕鼠器。两个人学到半夜,忍受屋子角落里老鼠猖狂地跑来跑去,发出吱吱叽叽的叫声,竟然觉得很有意思,捂着肚子笑了半天。
我们每一年都出去旅行一次,墨尔本,塔斯马尼亚岛,斐济,新加坡,最远的一次去了意大利。因为我们都喜欢《以你的名字呼唤我》。我们真的到了托斯卡纳的卢卡小镇,在镇上品了葡萄酒,她拿可乐汽水瓶盖偷了一点儿,端到罗马式的古教堂前,坐在喷泉边喂给我喝。
她咪一小口,我咪一小口。
天高云蓝,红酒汁儿黏在她唇边,油画般火烈,类似我们旷日持久的热恋。泉水哗哗淌着,折射耀眼的光芒,她坐在整个夏日前就像一位神祇。
在这片同性恋的朝圣之地,我们两个被原生家庭抛弃的人,头次真正放松下来,感到被彼此以外之物接纳。我决定这辈子都和眼前这个女孩子在一起。是女孩子,不是女人,她瘦瘦小小的,不论到了什么年纪都可以在我这里做一个小孩。
2.即便是患上艾滋
回到布里斯班后,日子重新开始正常运转。
我30岁生日那天,妈妈半夜在电话里崩溃,她像从前哄小孩那样给我唱生日歌,唱着唱着突然失声痛哭。我知道她在我面前假装开心很久,就像我在她面前假装性取向正常。她讲:“你30岁了,妈妈也老了,我什么时候能看到你结婚?你能不能让我死前看到你结婚?你离我好远,我经常半夜睡不着,担心你在南半球太孤单,担心你一辈子孤单下去。”
为了哄她,让她不要再哭,我讲我已经有了男友。
她半信半疑,说要飞到布里斯班亲眼看看。
在妈妈的飞机落地前,我紧急托朋友的朋友给我找了一位男同性恋。人高马大,文质彬彬。我们在机场接到妈妈,他喊阿姨,很绅士地上前拿行李,递过去他自己提前准备好的矿泉水。
妈妈问在一起多久了,我把和小辛在一起的日期告诉了她。
妈妈又问我们平时怎么相处,我把和小辛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告诉了她。
妈妈听完鼻子红红,眼里又有泪花,说:“你终于找到了你爱的,爱你的人。”我面上点头,心里感到一阵悲哀。妈妈看看我,又看看在开车的一表人材的男同,面露欣慰,话变得多了起来,一直在问东问西。她很少有话这么多的时候。
我把妈妈接回家,让男同先回去,把小辛介绍给妈妈,和她讲,这是我舍友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,妈妈和小辛相处得很愉快,她们从bunnings买了一堆花花草草回来搞园艺,绣球,芍药,淡粉的龙面花,洁白的香雪球,还有盆栽小辣椒,摆得阳台满满当当。我们三个人逛街,为对方挑选好看的口红,陪妈妈去chemist warehouse买一堆保健品,傍晚到布里斯班大桥边发呆。妈妈还教会我俩好多道她的拿手好菜,红烧紫排,油焖大虾,芋头焗肉。唯一的不愉快是每次做好一桌子菜,都要把男同喊到家里来吃。
我们演戏的时候,小辛就在旁边安静而机械地扒饭,一点儿声音都不出。她什么都没说,但我能够听见她眼泪滴在饭粒上的声音......
妈妈这次视察回国后,好像因为放下了心头很久的负担,整个人一下子垮了,身体变得很不好。她催我和男同结婚,她怕自己再也没机会看到我穿婚纱的样子。电话打了好多通,情绪不好的时候都哭哭啼啼。
3. 活下去,结婚
我和男同假结婚了两年。
平衡这段假婚姻和小辛之间的的关系让我精疲力尽,我也不再想为了迎合社会把本来很简单的爱情搞得这样糟糕,所以2017年的冬天,我离婚了,我32岁,我和小辛说:“去他妈的一切,我们不要回国了,我们永远留在这里!小辛,结婚吧,然后永远在一起。”
即使时常感到,不论在地球哪个角落,我们都人微言轻,但澳洲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度比国内要高很多,起码在这里,我和小辛可以到大街上相爱。
但是就在2017年决定要永远留下的时候,一次体检过后,小辛被发现HIV阳性也就是别人常说的艾滋......
健康地活着,对我们来讲,突然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。我和小辛抱头痛哭过,搞不明白生活对我俩怎么百般刁难。浑浑噩噩过了有一段时日,有一天从床上醒来,微凉的秋风吹进卧室,小辛突然很认真看着我,讲:“我还是好想要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婚礼,我想穿漂亮的婚纱裙,阳光明媚,你在我身边,三两宾客围在一块儿吃巧克力瀑布。
”
我抱着小辛嚎啕大哭。
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经我朋友的推荐和介绍,我和小辛坐在了澳洲最大华人律师事务所AHL法律的办公室里面,窗外一缕阳光洒在他们办公室柔软的波斯地毯上,我和小辛踩在这柔软的地毯上,在AHL法律的帮助下正式注册结婚了。
AHL法律的一位慈祥的胖律师拥抱了我们,宽慰地告诉我们不用担心,即便在新冠大流行期间,AHL法律的效率也很高。胖律师迅速地审阅了我们的医疗报告,监督我们3-6个月定期去clinic检查,了解我们病情稳定可控后将申请递交给了澳洲政府。
帮助我的律师是位负责任的女性,像我的妈妈,当她拥抱搂着我们的时候,我想到了我在远方的妈妈,她的手很柔软,很温柔,她轻声安慰我,会好起来的,那样的轻声细语,像数十年前,刚认识小辛时候她给我的温柔。
我的泪滴在了她的披肩上,那袭像我妈妈经常披的,带有四叶草图案的披肩......
To be continued
(本文根据AHL法律真实案件改编)
附:澳大利亚政府针对艾滋病患者配偶签证申请的特殊要求




 1300 91 66 77
1300 91 66 77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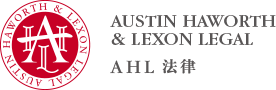






 首页
首页